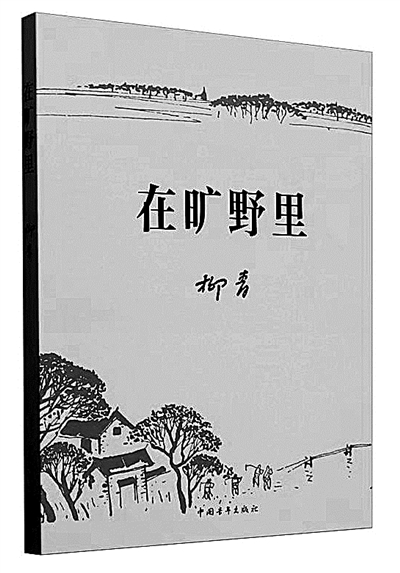|
||||||
风起旷野
——读柳青佚作《在旷野里》
◎ 王建华
2024年,柳青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发表和出版。我终于读到了这部珍藏了七十余年,至今依然醇香浓烈的作品。 小说的背景时间是1951年夏天,地点在陕西关中地区,主要围绕新到任的县委书记朱明山带领干部和群众治棉蚜虫害一事展开故事情节。柳青虽然在小说末尾标注“未完”,但实际上,他已经用真挚的情感、真实的故事和真诚的写作,将读者完全带入了那个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如火如荼的年代。 合上书,我的眼前还浮现着广袤丰饶的八百里秦川,耳畔还回响着劳动人民战天斗地的荡气回肠的声音,鼻孔里仿佛还能嗅到那混合了炊烟味、草木味的泥土气息。一群可亲可敬、可歌可泣的人儿,像风一样,从旷野走来,带着让人热血沸腾的振奋。 朱明山在工作中是典型的“实践派”,他以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很快为艰难的治虫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在他看来,能够从高级领导机关来到基层,虽然比不上那些去了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同志,以及到了朝鲜的战友们,但是,也总算实现“在工作中学习”了。这和柳青辞去县委副书记,深入群众开展创作是多么相似。可见,朱明山这个主要人物的背后,有着柳青的影子和理想。朱明山不搞形式主义,团结带领干部群众跟上新的时代的故事,就是柳青对新中国成立之初“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干部成长道路的艺术再现和思考。 创业的路,总是充满荆棘。治棉蚜虫害,是朱明山甫下火车遇到的一个难题。然而比棉蚜虫害更棘手的,是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作风问题。一方面,群众普遍存在迷信思想,宁愿请神祭拜虫王爷,也不相信工作队能把虫治好。另一方面,连白生玉这样的老区干部也背上了沉重的思想负担:“革命的饭总算吃下来了,建设的这碗饭,没文化没知识,恐怕不好吃。” 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柳青,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以文学的形式将这一时代问题抛了出来。这种敏锐的观察、深入的调查和真诚的写作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读的过程,让人不得不感叹:这哪里是小说,简直就是生活本真。一切都是柳青所熟悉的,从县委书记到植棉能手,从基层干部到人民群众,从农业生产到乡村风物,无一不是柳青扎根农村、走近人民、书写时代的结果。他怀着对人民的巨大热爱,用文字实践着“一切归根于生活”的铮铮话语。“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这位说到做到的人民作家,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干部、农民,再用如椽巨笔,把带着新鲜泥土气息的创业者群像,生动准确地安放在了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因为是未完成稿,小说似乎刚刚铺开宏大的叙事,就戛然而止。留给我们一连串问号:渭河南岸的群众最后发动起来了吗?赵振国、白生玉等老干部的思想包袱丢掉了吗?梁斌、郝凤歧等人的“思想害虫”治好没有?年轻的团委副书记李瑛最终心仪的对象是谁?甚至,朱明山与小说中从未正面登场的妻子高生兰之间,又有着怎样的结局?太多的意犹未尽,让读者的想象像风一般驰骋在旷野里。或许,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种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县委书记朱明山绝不会任由干部思想滑坡:“我们一定要教育干部,怎么把这种宝贵的热情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小说中,柳青除了真诚的叙事,也通过诗意的描写,把渭河平原的乡野景色描绘成一幅幅安然宁静的图画。正是在这样优美的田野里,村庄和树丛、炊烟和牛粪、月牙和繁星、河流和山脉见证了朱明山和治虫工作队怎样渡过渭河,走向“战场”。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村景乡情,带给人浓厚的亲切感。 读罢掩卷,仔细体味,便觉一阵浩荡春风正从渭河边、秦岭脚下生起,穿越时空迎面而来,驰骋在祖国大江南北,带给人无穷的希望和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