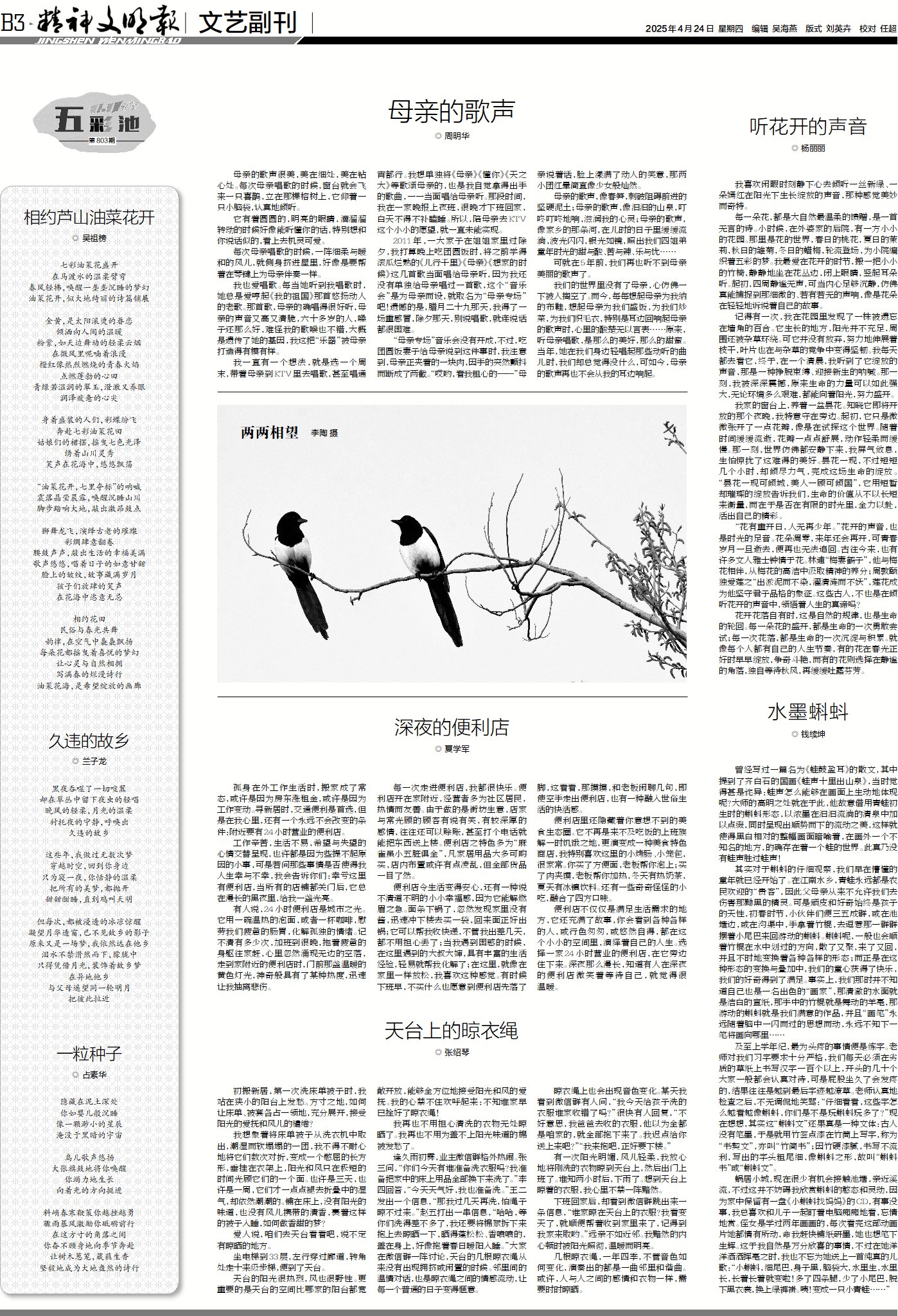|
||||||
水墨蝌蚪
◎ 钱续坤
曾经写过一篇名为《蛙鼓盈耳》的散文,其中提到了齐白石的国画《蛙声十里出山泉》,当时觉得甚是诧异:蛙声怎么能够在画面上生动地体现呢?大师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他故意借用青蛙初生时的蝌蚪形态,以浓墨在汩汩流淌的清泉中加以点缀,同时呈现出顺势而下的流动之美,这样就使得黑白相对的整幅画面暗喻着,在画外一个不知名的地方,的确存在着一个蛙的世界。此真乃没有蛙声胜过蛙声! 其实对于蝌蚪的仔细观察,我们早在懵懂的童年就已经开始了。在江南水乡,青蛙永远都是农民欢迎的“贵客”,因此父母亲从来不允许我们去伤害那黝黑的精灵。可是顽皮和好奇始终是孩子的天性,初春时节,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或在池塘边,或在沟渠中,手拿着竹棍,去逗惹那一群群摆着小尾巴来回游动的蝌蚪。蝌蚪呢,一般也会顺着竹棍在水中划过的方向,散了又聚,来了又回,并且不时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态;而正是在这种形态的变换与叠加中,我们的童心获得了快乐,我们的好奇得到了满足。事实上,我们那时并不知道自己也是一名出色的“画家”,那清澈的水面就是洁白的宣纸,那手中的竹棍就是舞动的羊毫,那游动的蝌蚪就是我们满意的作品,并且“画笔”永远随着脑中一闪而过的思想而动,永远不知下一笔将画向哪里…… 及至上学年纪,最为头疼的事情便是练字。老师对我们习字要求十分严格,我们每天必须在劣质的草纸上书写汉字一百个以上,开头的几十个大家一般都会认真对待,可是屁股坐久了会发疼的,结果往往是越到最后字迹越潦草。老师认真地检查之后,不无调侃地笑骂:“仔细看看,这些字怎么越看越像蝌蚪,你们是不是玩蝌蚪玩多了?”现在想想,其实这“蝌蚪文”还果真是一种文体:古人没有笔墨,于是就用竹签点漆在竹筒上写字,称为“书契文”,亦叫“竹简书”;因竹硬漆腻,书写不流利,写出的字头粗尾细,像蝌蚪之形,故叫“蝌蚪书”或“蝌蚪文”。 蜗居小城,现在很少有机会接触池塘,亲近溪流,不过这并不妨碍我欣赏蝌蚪的憨态和灵动,因为家中保留有一盘《小蝌蚪找妈妈》的CD,有事没事,我总喜欢和儿子一起盯着电脑痴痴地看,忘情地赏。侄女是学过两年画画的,每次看完这部动画片她都情有所动,命我赶快铺纸研墨,她也想笔下生辉。这于我自然是万分欣喜的事情,不过在她洋洋洒洒挥毫之时,我也不忘为她送上一首纯真的儿歌:“小蝌蚪,细尾巴,身子黑,脑袋大,水里生,水里长,长着长着就变啦!多了四条腿,少了小尾巴,脱下黑衣裳,换上绿裤褂。咦!变成一只小青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