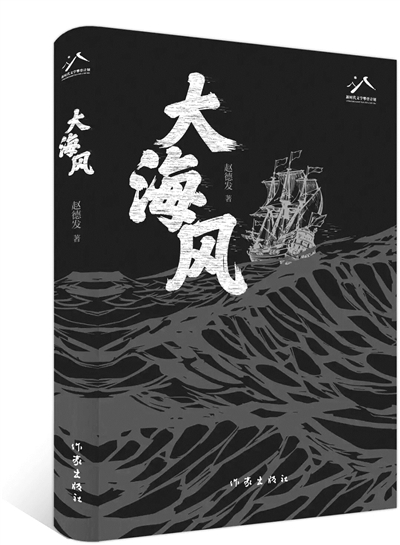|
||||||
在风浪中照亮生命的航向
◎ 黄伟兴
赵德发的《大海风》以黄海之滨为叙事舞台,描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的渔业和航运历史。这部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长篇力作,以50余万字的宏阔篇幅,重构了北方渔业的兴衰轨迹。全书更以“海立云垂”的叙事张力,将个体命运、家族传奇与民族危局熔铸为一部关于生存、抗争与觉醒的海洋史诗。 小说以黄海之滨的马蹄所渔村为核心,串联青岛、上海、大连等港口城市及广袤海域,描写20世纪上半叶中国北方渔业的历史图景。小说深刻映现人海关系的时代变迁,既浓墨重彩描绘主人公面对疾风巨浪时的坚韧品格与进取姿态、外敌入侵时的家国情怀与牺牲精神,又穿插扣人心弦的航海传奇,将斑斓多姿的渔家风情娓娓道来,于波涛深处留下一处时代的生命印记。 小说开篇以一场夺走十二条人命的海难切入,让海洋成为故事的关键角色——它既是孕育文明的根基,亦是磨砺精神的试炼场。邢昭衍自幼听着父亲“靠海吃海”的教诲长大,勇于担当的他在海难之后毅然卖掉家中田地造大船。这种与传统观念相悖的抉择,恰是海洋力量对陆地生存逻辑的突破性叩击。 作者笔下细腻呈现“血网”“祭海神”等海滨老习俗,将渔民与大海的依存关系升华为精神层面的契约。如梭子姐妹在暴风雨中以渔歌对抗死神,邢昭衍沉船前听见龙神庙檐角铁马的叮咚声。此刻的海洋不再仅是自然景观,而是成为承载集体记忆与文化传承的活态符号,在潮起潮落间诉说着人与海的千年羁绊。 书中充盈着海洋精神的具象呈现,在小说后半段抵达高潮。面对日军侵华的铁蹄,邢昭衍将苦心经营的船队沉入海底。这一充满悲剧美学的抉择,实则是海洋文明在民族危亡时刻的终极奉献。正如作者所说的“海洋也是淬炼人性的地方”,当木船在侵略者的汽笛声中沦为历史垫脚石,当实业救国的理想在民族危亡前破碎,书中以沉船意象完成了对海洋精神的生动阐释。 小说构建起青岛洋行的玻璃柜台与海暾县龙神庙的袅袅香火景象空间,让读者沉浸其中。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翻译《论语》的场景,与靖先生在礼贤书院讲授《海国图志》的情节彼此呼应,暗喻东西方文明在黄海之滨的相遇与对话。这种文化碰撞在邢昭衍身上形成奇妙张力:他既能用德语与洋商在谈判桌前博弈,又坚持在船头悬挂“妈祖保佑”的杏黄旗;既效仿张謇创办近代航运实业,又恪守渔家古训——这种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精神杂糅,增添了海洋文明的包容性与复杂性。 在历史的大风大浪里,作者一直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邢昭衍的创业故事不是传统的英雄赞歌,而是充满艰难险阻的航程:被恶霸砸坏的渔船、被土匪绑架的妻儿、被官府克扣的税银,这些苦难不单单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是形成了更为厚实的人物性格。当他在雪夜看见梭子冻成冰柱还紧握着渔网,当他看到船老大望天晌在台风里跟船一起沉没,这些瞬间闪现的人性光芒,照亮了历史黑暗中人们精神突围的路。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引人注意,她们既有着“拿得起生活重担”的坚韧,也有着“放得下陈规束缚”的果敢。翟蕙反对父母包办婚姻选择逃婚,梭子在鱼市上与买家讨价还价,杏花织网时吟唱着《大海风》的民谣……这些看似寻常的生活场景,实则是女性意识觉醒的缩影。全书没有沿用传统海洋题材中“海嫂”的悲情叙事套路,而是星星点点描绘出她们如海浪般的坚韧。 如今生态问题愈发凸显,《大海风》中对海洋生态的描写便颇具前瞻性。书里既细致描摹了鱼群洄游的景象,也讲述了民间对“鬼潮”现象的认知,足见作者的用心观察。这种生态视角不仅让小说内容更为丰满,更蕴含着对海洋文明的深层思考。 小说《大海风》兼具历史、地理细节以及人文深度,是了解海洋文化的重要窗口。载着渔歌与汽笛的回响,在历史与现实的浪潮中航行,赵德发以海洋为墨、命运为笔,书写了这部关于民族生存、抗争与觉醒的壮阔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