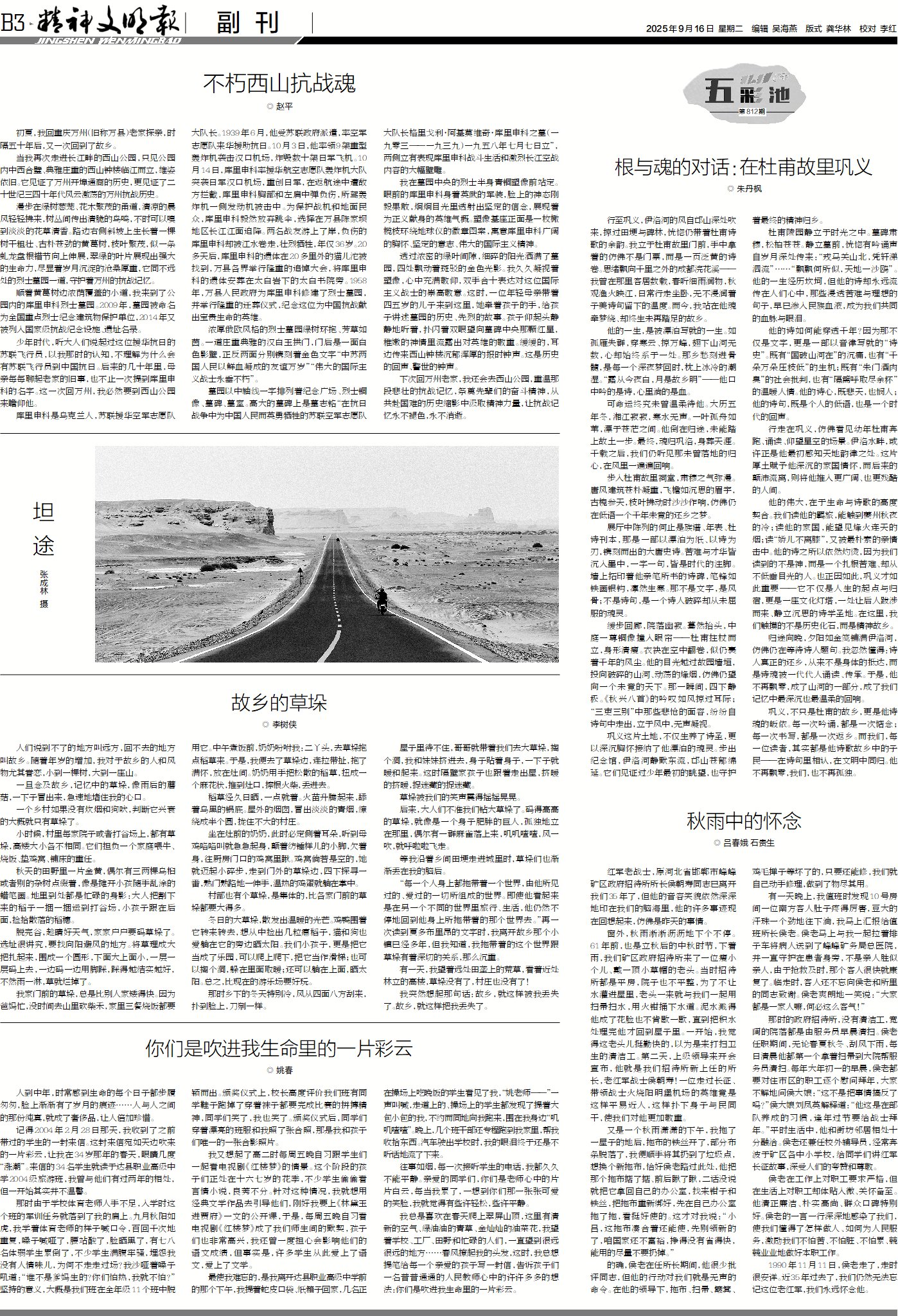|
||||||
根与魂的对话:在杜甫故里巩义
◎ 朱丹枫
行至巩义,伊洛河的风自邙山深处吹来,掠过田埂与碑林,恍惚仍带着杜甫诗歌的余韵。我立于杜甫故里门前,手中拿着的仿佛不是门票,而是一页泛黄的诗卷。思绪飘向千里之外的成都浣花溪——我曾在那里客居数载,春听细雨润物,秋观渔火映江,日常行走坐卧,无不浸润着子美诗句留下的温度。而今,我站在他魂牵梦绕、却终生未再踏足的故乡。 他的一生,是被漂泊写就的一生。如孤雁失群,穿寒云、掠万峰,翅下山河无数,心却始终系于一处。那乡愁刻进骨髓,是每一个深夜梦回时,枕上冰冷的潮湿。“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他口中吟的是诗,心里淌的是血。 可命运终究未曾温柔待他。大历五年冬,湘江寂寂,寒水无声。一叶孤舟如苇,漂于苍茫之间。他倒在归途,未能踏上故土一步。最终,魂归巩洛,身葬天涯。千载之后,我们仍听见那未曾落地的归心,在风里一遍遍回响。 步入杜甫故里祠堂,肃穆之气弥漫。唐风建筑苍朴凝重,飞檐如沉思的眉宇,古槐参天,枝叶拂动时沙沙作响,仿佛仍在低语一个千年未竟的还乡之梦。 展厅中陈列的何止是族谱、年表、杜诗刊本,那是一部以漂泊为纸、以诗为刃,镌刻而出的大唐史诗。苦难与才华皆沉入墨中,一字一句,皆是时代的注脚。墙上拓印着他亲笔所书的诗碑,笔锋如铁画银钩,凛然生寒。那不是文字,是风骨;不是诗句,是一个诗人破碎却从未屈服的魂灵。 缓步回廊,院落幽寂。蓦然抬头,中庭一尊铜像撞入眼帘——杜甫拄杖而立,身形清瘦。衣袂在空中翻卷,似仍裹着千年的风尘。他的目光越过故园墙垣,投向破碎的山河、动荡的烽烟,仿佛仍望向一个未竟的天下。那一瞬间,四下静极。《秋兴八首》的吟叹如风掠过耳际;“三吏三别”中那些悲怆的面容,纷纷自诗句中走出,立于风中,无声凝视。 巩义这片土地,不仅生养了诗圣,更以深沉胸怀接纳了他漂泊的魂灵。步出纪念馆,伊洛河静默东流,邙山苍郁绵延。它们见证过少年最初的眺望,也守护着最终的精神归乡。 杜甫陵园静立于时光之中。墓碑肃穆,松柏苍苍。静立墓前,恍惚有吟诵声自岁月深处传来:“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的一生经历坎坷,但他的诗却永远流传在人们心中,那些浸透苦难与理想的句子,早已渗入民族血液,成为我们共同的血脉与眼泪。 他的诗如何能穿透千年?因为那不仅是文字,更是一部以音律写就的“诗史”。既有“国破山河在”的沉痛,也有“千朵万朵压枝低”的生机;既有“朱门酒肉臭”的社会批判,也有“隔篱呼取尽余杯”的温暖人情。他的诗心,既悲天,也悯人;他的诗句,既是个人的低语,也是一个时代的回声。 行走在巩义,仿佛看见幼年杜甫奔跑、诵读、仰望星空的场景。伊洛水畔,或许正是他最初感知天地韵律之处。这片厚土赋予他深沉的家国情怀,而后来的颠沛流离,则将他推入更广阔、也更残酷的人间。 他的伟大,在于生命与诗歌的高度契合。我们读他的羁旅,能触到夔州秋夜的冷;读他的家国,能望见烽火连天的烟;读“娇儿不离膝”,又被最朴素的亲情击中。他的诗之所以依然灼烫,因为我们读到的不是神,而是一个扎根苦难、却从不低垂目光的人。也正因如此,巩义才如此重要——它不仅是人生的起点与归宿,更是一座文化灯塔,一处让后人跋涉而来、静立沉思的诗学圣地。在这里,我们触摸的不是历史化石,而是精神故乡。 归途向晚,夕阳如金笺铺满伊洛河,仿佛仍在等待诗人题句。我忽然懂得:诗人真正的还乡,从来不是身体的抵达,而是诗魂被一代代人诵读、传承。于是,他不再飘零,成了山河的一部分,成了我们记忆中最深沉也最温柔的回响。 巩义,不只是杜甫的故乡,更是他诗魂的皈依。每一次吟诵,都是一次惦念;每一次书写,都是一次返乡。而我们,每一位读者,其实都是他诗歌故乡中的子民——在诗句里相认,在文明中同归。他不再飘零,我们,也不再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