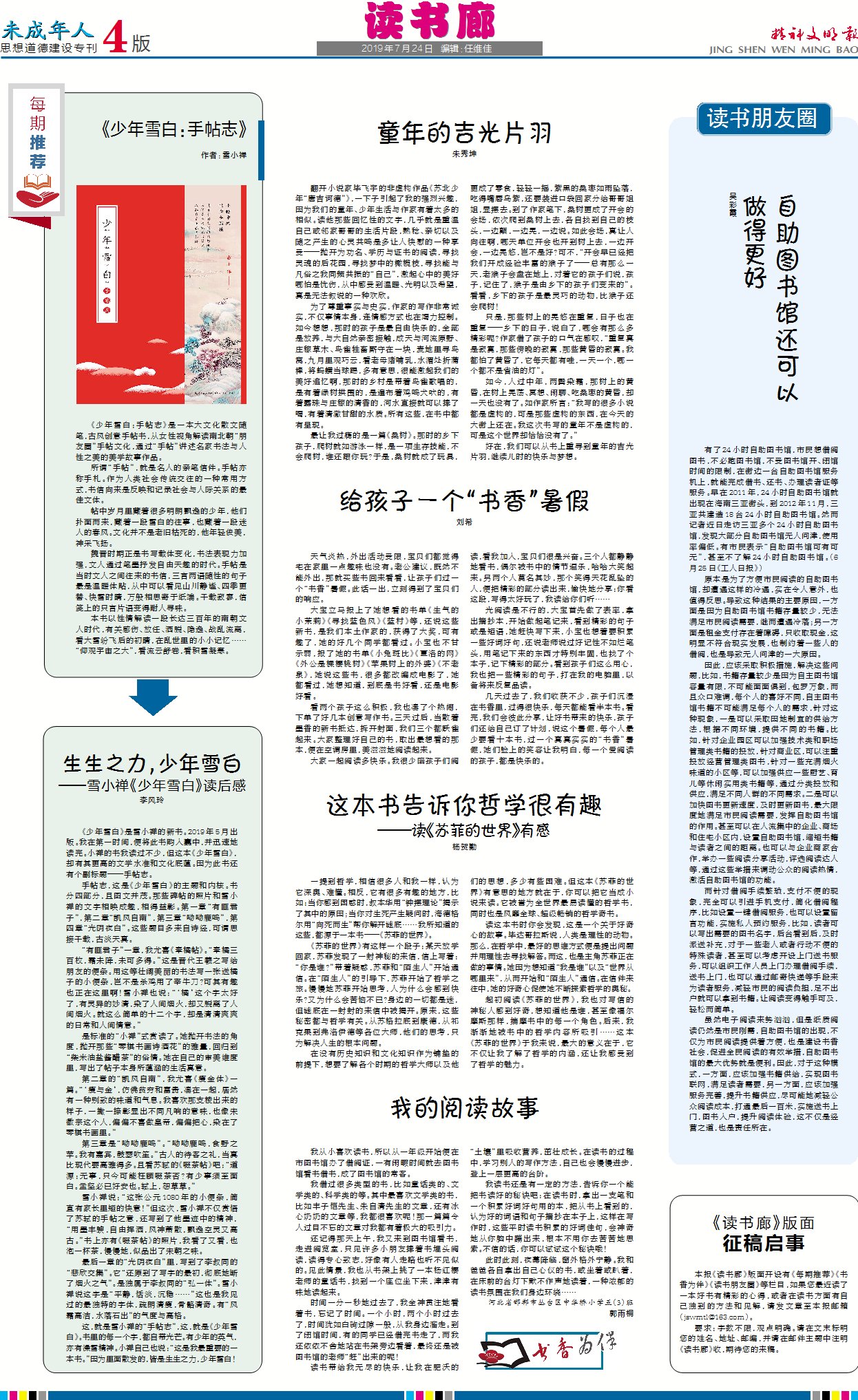|
||||||
童年的吉光片羽
朱秀坤
翻开小说家毕飞宇的非虚构作品《苏北少年“唐吉诃德”》,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强烈兴趣,因为我们的童年、少年生活与作家有着太多的相似。读他那些回忆性的文字,几乎就是重温自己或邻家哥哥的生活片段,熟稔、亲切以及随之产生的心灵共鸣是多让人快慰的一种享受——抛开为功名、学历与证书的阅读,寻找灵魂的后花园,寻找梦中的橄榄枝,寻找能与凡俗之我同频共振的“自己”,激起心中的美好哪怕是忧伤,从中感受到温暖、光明以及希望,真是无法叙说的一种欢欣。 为了尊重事实与史实,作家的写作非常诚实,不仅事情本身,连情感方式也在竭力控制。如今想想,那时的孩子是最自由快乐的,全部是放养,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成天与河流原野、庄稼草木、鸟雀牲畜厮守在一块,麦地里寻鸟窝,九月里观巧云,看老母猪哺乳,水湄处折蒲棒,将蚂蟥当球踢,多有意思,很能激起我们的美好追忆啊,那时的乡村是带着鸟雀歌唱的,是有着绿树拱围的,是遍布着鸡鸣犬吠的,有着露珠与庄稼的清香的,河水直接就可以捧了喝,有着清澈甘甜的水质。所有这些,在书中都有呈现。 最让我过瘾的是一篇《桑树》。那时的乡下孩子,爬树就如游泳一样,是一项生存技能,不会爬树,谁还跟你玩?于是,桑树就成了玩具,更成了零食,轻轻一摇,紫黑的桑枣如雨坠落,吃得嘴唇乌紫,还要装进口袋回家分给哥哥姐姐,显摆去。到了作家笔下,桑树更成了开会的会场,依次爬到桑树上去,各自找到自己的枝头,一边颠,一边晃,一边说。如此会场,真让人向往啊,哪天单位开会也开到树上去,一边开会,一边晃悠,岂不是好?可不,“开会早已经把我们开成经验丰富的猴子了——总有那么一天,老猴子会盘在地上,对着它的孩子们说,孩子,记住了,猴子是由乡下的孩子们变来的”。看看,乡下的孩子是最灵巧的动物,比猴子还会爬树! 只是,那些树上的晃悠在重复,日子也在重复——乡下的日子,说白了,哪会有那么多精彩呢?作家借了孩子的口气在感叹,“重复真是寂寞,那些傍晚的寂寞,那些黄昏的寂寞。我都怕了黄昏了,它每天都有哇,一天一个,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如今,人过中年,两鬓染霜,那树上的黄昏,在树上晃荡、冥想、闲聊、吃桑枣的黄昏,却一天也没有了。如作家所言:“我写的很多小说都是虚构的,可是那些虚构的东西,在今天的大街上还在。我这次书写的童年不是虚构的,可是这个世界却恰恰没有了。” 好在,我们可以从书上重寻到童年的吉光片羽,继续儿时的快乐与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