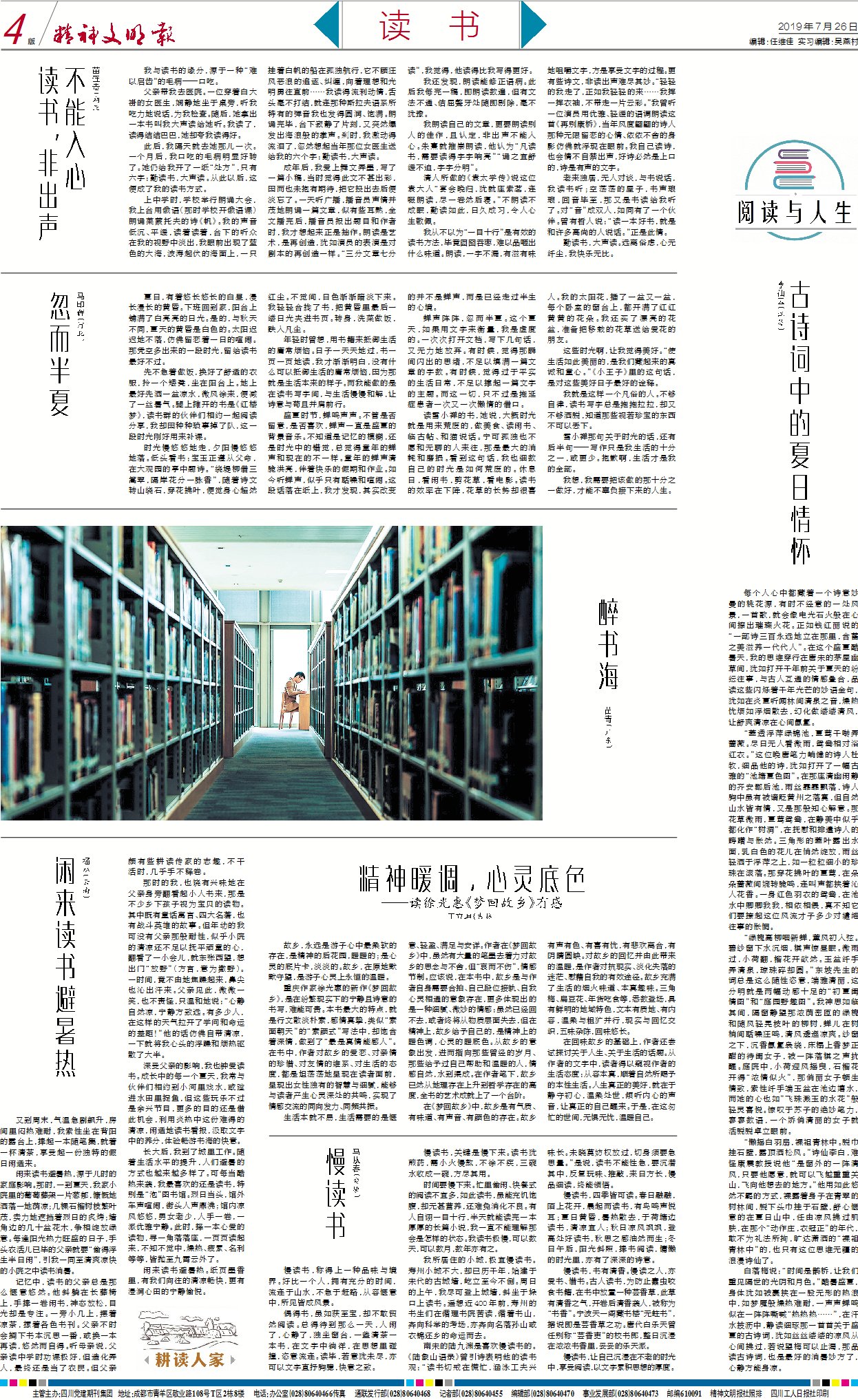|
||||||
读书,非出声不能入心
苗连贵(湖北)
我与读书的缘分,源于一种“难以启齿”的毛病——口吃。 父亲带我去医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女医生,娴静地坐于桌旁,听我吃力地说话,为我检查。随后,她拿出一本书叫我大声读给她听。我读了,读得结结巴巴,她却夸我读得好。 此后,我隔天就去她那儿一次。一个月后,我口吃的毛病明显好转了。她仍给我开了一纸“处方”,只有六字:勤读书,大声读。从此以后,这便成了我的读书方式。 上中学时,学校举行朗诵大会,我上台用俄语(那时学校开俄语课)朗诵莱蒙托夫的诗《帆》。我的声音低沉、平缓,读着读着,台下的听众在我的视野中淡出,我眼前出现了蓝色的大海,波涛起伏的海面上,一只挂着白帆的船在孤独航行,它不顾狂风恶浪的追逐、纠缠,向着理想和光明勇往直前……我读得流利动情,舌头毫不打结,就连那种斯拉夫语系所特有的弹音我也发得圆润、饱满。朗诵完毕,台下寂静了片刻,又突然爆发出海浪般的掌声。剎时,我激动得流泪了,忽然想起当年那位女医生送给我的六个字:勤读书,大声读。 成年后,我爱上舞文弄墨,写了一篇小稿,当时觉得此文不甚出彩,因而也未抱有期待,把它投出去后便淡忘了。一天听广播,播音员声情并茂地朗诵一篇文章,似有些耳熟,全文播完后,播音员报出题目和作者时,我才想起来正是拙作。朗读是艺术,是再创造,犹如演员的表演是对剧本的再创造一样。“三分文章七分读”,我觉得,他读得比我写得更好。 我还发现,朗读能修正语病。此后我每完一稿,即朗读数遍,但有文法不通、佶屈聱牙处随即剔除,毫不犹豫。 我朗读自己的文章,更要朗读别人的佳作,且认定,非出声不能入心。朱熹就推崇朗读,他认为“凡读书,需要读得字字响亮”“诵之宜舒缓不迫,字字分明”。 清人所做的《袁太学传》说这位袁大人“宴会晚归,犹就座索茗,连啜朗读,尽一卷然后寝。”不朗读不成眠,勤读如此,日久成习,令人心生敬佩。 我从不以为“一目十行”是有效的读书方法,毕竟囫囵吞枣,难以品咂出什么味道。朗读,一字不漏,有滋有味地咀嚼文字,方是享受文字的过程。更有些诗文,非读出声难尽其妙。“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曾听一位演员用优雅、轻缓的语调朗读这首《再别康桥》,当年风度翩翩的诗人那种无限留恋的心情、依依不舍的身影仿佛就浮现在眼前。我自己读诗,也会情不自禁出声,好诗必然是上口的,诗是有声的文字。 老来独居,无人对谈,与书说话,我读书听;空荡荡的屋子,书声琅琅,回音毕至,那又是书读给我听了。对“音”成双人,如同有了一个伙伴。曾有哲人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说话。”正是此情。 勤读书,大声读。远离俗虑,心无纤尘,我快乐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