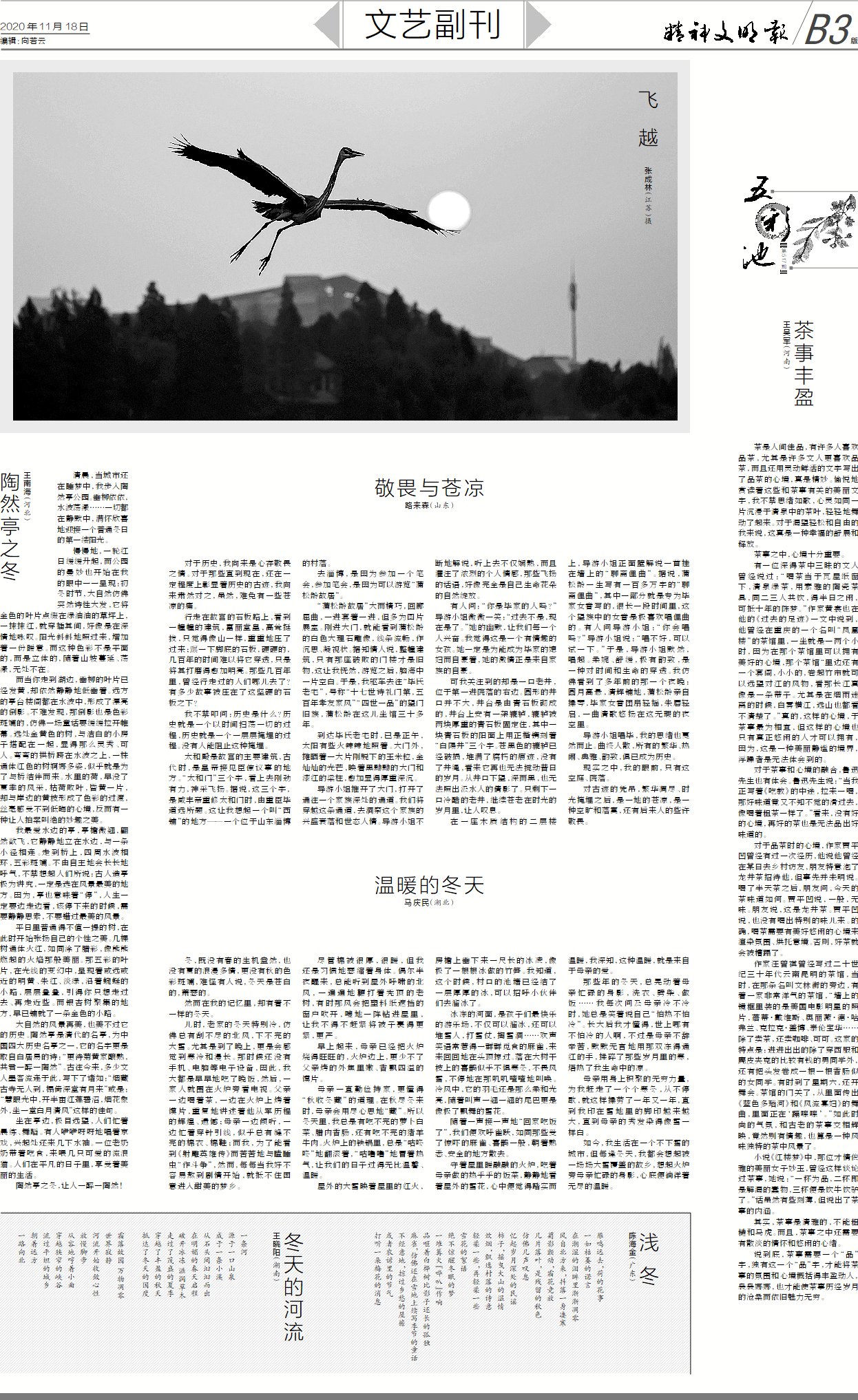|
||||||
敬畏与苍凉
路来森(山东)
对于历史,我向来是心存敬畏之情。对于那些直到现在,还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历史的古迹,我向来肃然对之,虽然,难免有一些苍凉的痛。 行走在故宫的石板路上,看到一幢幢的建筑,富丽堂皇,高耸挺拔,只觉得像山一样,重重地压了过来;蹍一下脚底的石板,硬硬的,几百年的时间难以将它穿透,只是将其打磨得愈加明亮。那些几百年里,曾经行走过的人们哪儿去了?有多少故事被压在了这坚硬的石板之下? 我不禁叩问: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个以时间扫荡一切的过程,历史就是一个一层层掩埋的过程。没有人能阻止这种掩埋。 太和殿是故宫的主要建筑,古代时,是皇帝接见臣僚议事的地方。“太和门”三个字,看上去刚劲有力,神采飞扬。据说,这三个字,是咸丰帝重修太和门时,由重臣毕道远所题。这让我想起一个叫“西铺”的地方——一个位于山东淄博的村落。 去淄博,是因为参加一个笔会,参加笔会,是因为可以游览“蒲松龄故居”。 “蒲松龄故居”大而精巧,回廊屈曲,一进套着一进,但多为图片展室。刚进大门,就能看到蒲松龄的白色大理石雕像,线条流畅,作沉思、凝视状。据知情人说,整幢建筑,只有那座破败的门楼才是旧物,这让我怃然,游览之后,脑海中一片空白。于是,我驱车去往“毕氏老宅”,号称“十七世诗礼门第,五百年孝友家风”“四世一品”的望门旧族,蒲松龄在这儿坐馆三十多年。 到达毕氏老宅时,已是正午,太阳有些火辣辣地照着。大门外,摊晒着一大片刚脱下的玉米粒,金灿灿的光芒,映着黑黝黝的大门和漆红的梁柱,愈加显得厚重深沉。 导游小姐推开了大门,打开了通往一个家族深处的通道。我们将穿越这条通道,去洞察这个家族的兴盛衰落和世态人情。导游小姐不断地解说,听上去不仅娴熟,而且灌注了浓烈的个人情感,那些飞扬的话语,好像完全是自己生命花朵的自然绽放。 有人问:“你是毕家的人吗?”导游小姐微微一笑:“过去不是,现在是了。”她的幽默,让我们每一个人兴奋。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情趣的女孩。她一定是为能成为毕家的媳妇而自豪着,她的激情正是来自家族的自豪。 可我关注到的却是一口老井,位于第一进院落的右边。圆形的井口并不大,井台是由青石板砌成的,井台上安有一架辘轳,辘轳被两块厚重的青石板固定住,其中一块青石板的阳面上用正楷镌刻着“白陽井”三个字。苍黑色的辘轳已经破损,堆满了腐朽的痕迹,没有了井绳,看来它再也无法搅动昔日的岁月。从井口下望,深而黑,也无法照出汲水人的倩影了。只剩下一口冷酷的老井,继续苍老在时光的岁月里,让人叹息。 在一座木质结构的二层楼上,导游小姐正面壁解说一首挂在墙上的“聊斋俚曲”。据说,蒲松龄一生写有一百多万字的“聊斋俚曲”,其中一部分就是专为毕家女眷写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望族中的女眷是极喜欢唱俚曲的。有人问导游小姐:“你会唱吗?”导游小姐说:“唱不好,可以试一下。”于是,导游小姐默然,唱起。柔婉、舒缓,极有韵致,是一种对时间和生命的穿透。我仿佛看到了多年前的那一个夜晚:圆月高悬,清辉铺地,蒲松龄亲自操琴,毕家女眷团扇轻摇,朱唇轻启,一曲清歌悠扬在这无瑕的夜空里。 导游小姐唱毕,我的思绪也戛然而止。曲终人散,所有的繁华、热闹、典雅、韵致,俱已成为历史。 现实之中,我的眼前,只有这空庭、院落。 对古迹的凭吊,繁华凋尽、时光掩埋之后,是一地的苍凉,是一种空旷和落寞,还有后来人的些许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