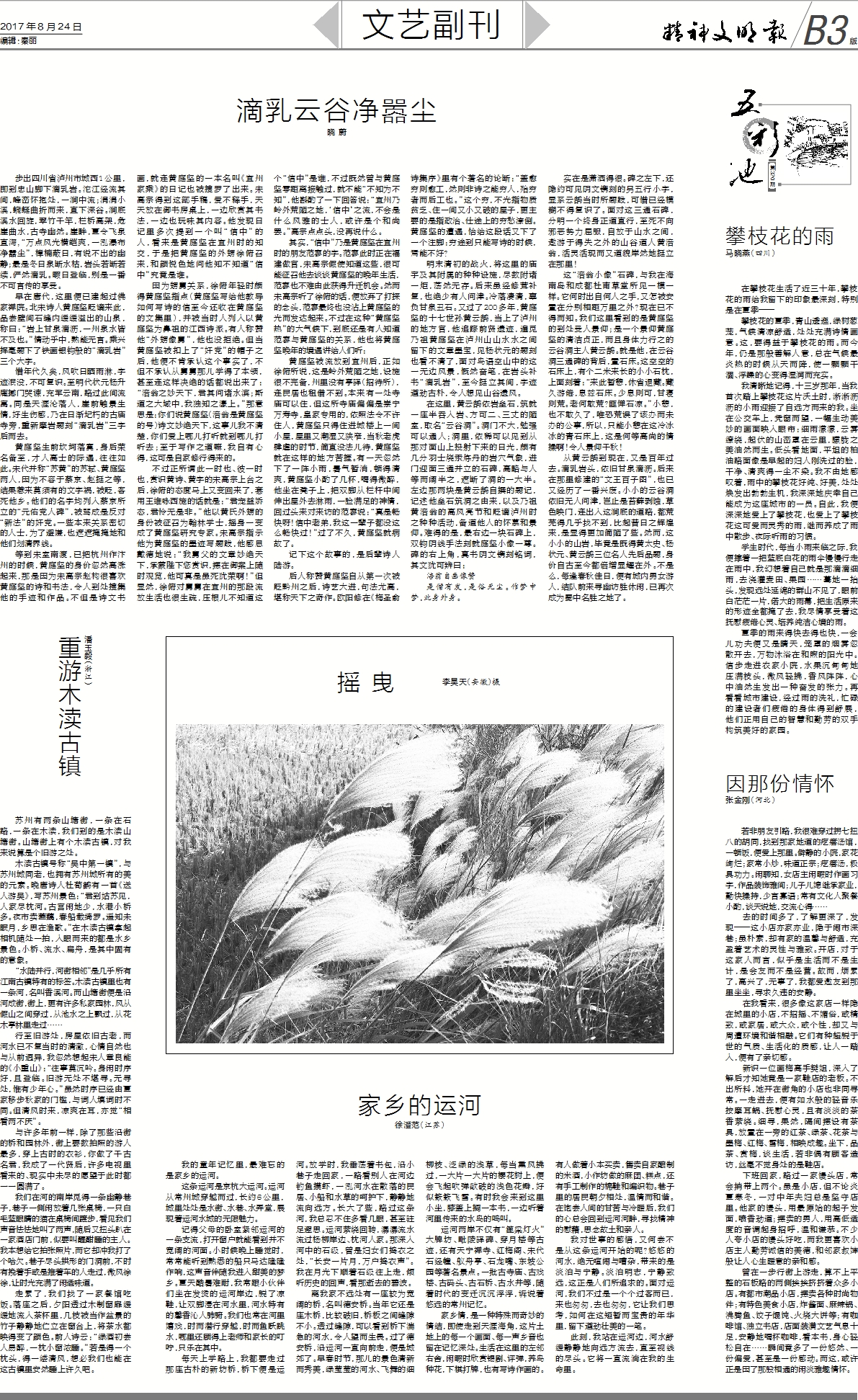|
||||||
滴乳云谷净嚣尘
晓 蔚
步出四川省泸州市城西1公里,即到忠山脚下滴乳岩。沱江经流其间,峰峦怀抱处,一涧中流;涓涓小溪,蜿蜒曲折而来,直下深谷。涧底溪水回旋,翠竹千竿,栏桥高架,危崖曲水,古寺幽然。崖畔,夏令飞泉直泻,“万点风光横皑爽,一泓瀑布净嚣尘”,樟楠蔽日,有说不出的幽静;最是冬日泉断水枯,岩头若断若续,俨然滴乳。暇日登临,别是一番不可言传的享受。
早在唐代,这里便已建起过佛家禅院。北宋诗人黄庭坚贬谪来此,品尝壁间石缝内缓缓溢出的山泉,称曰:“岩上甘泉滴沥,一州泉水皆不及也。”情动乎中,熟能无言。乘兴挥毫题下了铁画银钩般的“滴乳岩”三个大字。 惜年代久矣,风吹日晒雨淋,字迹泯没,不可复识。至明代状元杨升庵撼门哭谏,充军云南,路过此间流寓。同是天涯沦落人,崖前触景生情,好生伤感,乃在日渐圮朽的古庙寺旁,重新摩岩题刻“滴乳岩”三字后而去。 黄庭坚生前坎坷落寞,身后荣名备至,才人高士的际遇,往往如此。宋代并称“苏黄”的苏轼、黄庭坚两人,因为不容于蔡京、赵挺之等,结果惹来莫须有的文字祸,被贬,客死他乡。他们的名字均列入蔡京所立的“元佑党人碑”,被骂成是反对“新法”的奸党。一些本来关系密切的人士,为了避嫌,也遮遮掩掩地和他们划清界线。 等到宋室南渡,已把杭州作汴州的时候,黄庭坚的身价忽然高涨起来,那是因为宋高宗赵构很喜欢黄庭坚的诗和书法,令人到处搜集他的手迹和作品。不但是诗文书画,就连黄庭坚的一本名叫《宜州家乘》的日记也被搜罗了出来。宋高宗得到这部手稿,爱不释手,天天放在御书房桌上,一边欣赏其书法,一边也玩味其内容。他发现日记里多次提到一个叫“信中”的人,看来是黄庭坚在宜州时的知交,于是把黄庭坚的外甥徐俯召来,和颜悦色地问他知不知道“信中”究竟是谁。 因为甥舅关系,徐俯年轻时颇得黄庭坚指点(黄庭坚写给他教导如何写诗的信至今还收在黄庭坚的文集里),并被当时人列入以黄庭坚为鼻祖的江西诗派。有人称赞他“外甥像舅”,他也没拒绝。但当黄庭坚被扣上了“奸党”的帽子之后,他便不肯承认这个事实了,不但不承认从舅舅那儿学得了本领,甚至连这样决绝的话都说出来了:“涪翁之妙天下,君其问诸水滨;斯道之大域中,我独知之濠上。”那意思是:你们说黄庭坚(涪翁是黄庭坚的号)诗文妙绝天下,这事儿我不清楚,你们爱上哪儿打听就到哪儿打听去;至于写作之道嘛,我自有心得,这可是自家修行得来的。 不过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赏识黄诗、黄字的宋高宗上台之后,徐俯的态度马上又变回来了,套用王维咏西施的话就是:“君宠益娇态,君怜无是非。”他以黄氏外甥的身份被征召为翰林学士,摇身一变成了黄庭坚研究专家。宋高宗指示他为黄庭坚的墨迹写题跋,他感恩戴德地说:“我舅父的文章妙绝天下,承蒙陛下您赏识,摆在御案上随时观览,他可真是虽死犹荣啊!”但显然,徐俯对舅舅在宜州的那段流放生活也很生疏,压根儿不知道这个“信中”是谁,不过既然曾与黄庭坚零距离接触过,就不能“不知为不知”,他斟酌了一下回答说:“宜州乃岭外荒陋之地,‘信中’之流,不会是什么风雅的士人,或许是个和尚罢。”高宗点点头,没再说什么。 其实,“信中”乃是黄庭坚在宜州时的朋友范寥的字。范寥此时正在福建做官,宋高宗假使知道这些,很可能征召他去谈谈黄庭坚的晚年生活,范寥也不难由此获得升迁机会。然而宋高宗听了徐俯的话,便放弃了打探的念头,范寥最终也没沾上黄庭坚的光而发达起来。不过在这种“黄庭坚热”的大气候下,到底还是有人知道范寥与黄庭坚的关系,他也将黄庭坚晚年的境遇讲给人们听: 黄庭坚被流放到宜州后,正如徐俯所说,这是岭外荒陋之地,设施很不完备,州里没有亭驿(招待所),连民居也租借不到。本来有一处寺庙可以住,但这所寺庙偏偏是崇宁万寿寺,皇家专用的,依照法令不许住人,黄庭坚只得住进城楼上一间小屋,屋里又潮湿又狭窄,当秋老虎肆虐的时节,简直没法儿待,黄庭坚就在这样的地方苦捱。有一天忽然下了一阵小雨,暑气暂消,顿得清爽,黄庭坚小酌了几杯,喝得微醉,他坐在凳子上,把双脚从栏杆中间伸出屋外去淋雨,一脸满足的神情,回过头来对来访的范寥说:“真是畅快呀!信中老弟,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畅快过!”过了不久,黄庭坚就病故了。 记下这个故事的,是后辈诗人陆游。 后人称赞黄庭坚自从第一次被贬黔州之后,诗艺大进,句法尤高,堪称天下之奇作。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里有个著名的论断:“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这个穷,不光指物质贫乏、住一间又小又破的屋子,更主要的是指政治、仕途上的穷愁潦倒。黄庭坚的遭遇,恰给这段话又下了一个注脚:穷途到只能写诗的时候,焉能不好? 明末清初的战火,将这里的庙宇及其附属的种种设施,尽数附诸一炬,荡然无存。后来虽经修茸补复,也绝少有人问津。冷落凄清,辜负甘泉丑石。又过了200多年,黄庭坚的十七世孙黄云鹄,当上了泸州的地方官,他追踪前贤遗迹,遍觅乃祖黄庭坚在泸州山山水水之间留下的文章墨宝,见杨状元的题刻也看不清了,面对鸟语空山中的这一无边风景,慨然奋笔,在岩头补书“滴乳岩”,至今挺立其间,字迹遒劲古朴,令人想见山谷遗风。 在这里,黄云鹄依岩垒石,筑就一座半吞入岩、方可二、三丈的陋室,取名“云谷洞”。洞门不大,勉强可以通人;洞里,依稀可以见到从那对面山上投射下来的日光,颇有几分羽士烧汞炼丹的岩穴气象,进门迎面三通并立的石碑,高略与人等而阔半之,遮断了洞的一大半。左边那两块是黄云鹄自撰的题记,记述他垒石筑洞之由来,以及乃祖黄涪翁的高风亮节和贬谪泸州时之种种活动,备道他人的怀慕和景仰。难得的是,最右边一块石碑上,双钩阴线手法刻就庭坚小像一尊。碑的右上角,真书阴文镌刻铭词,其文犹可辨曰: 涪翁自画像赞 是僧有发,是俗无尘。作梦中梦,此身外身。 实在是潇洒得很。碑之左下,还隐约可见阴文镌刻的另五行小字,显系云鹄当时所题跋,可惜已经模糊不得复识了。面对这三通石碑,分明一个终身正道直行,至死不向邪恶势力屈服,自放于山水之间,遨游于得失之外的山谷道人黄涪翁,活灵活现而又道貌岸然地挺立在那里! 这“涪翁小像”石碑,与我在海南岛和成都杜甫草堂所见一模一样。它何时出自何人之手,又怎被安置在分别相距万里之外?现在已不得而知。我们这里看到的是黄庭坚的到处受人景仰;是一个景仰黄庭坚的清洁贞正,而且身体力行之的云谷洞主人黄云鹄。就是他,在云谷洞三通碑的背后,置石床。这空空的石床上,有个二米来长的小小石枕,上面刻着:“来此暂憩,休省退藏。藏久游倦,息兹石床。少息则可,甘寝则荒。老何敢荒?匪惮石凉。”小憩,也不敢久了,唯恐荒误了该办而未办的公事,所以,只能小憩在这冷冰冰的青石床上,这是何等高尚的情操啊!令人景仰千秋! 从黄云鹄到现在,又是百年过去。滴乳岩头,依旧甘泉滴沥。后来在那里修建的“文王百子图”,也已又经历了一番兴废。小小的云谷洞依旧无人问津,岂止是苔藓剥蚀,草色映门,连出入这涧底的道路,都荒芜得几乎找不到,比起昔日之辉煌来,是显得更加简陋了些。然而,这小小的山岩,毕竟是既得黄太史、杨状元、黄云鹄三位名人先后品题,身价自古至今都倍增显耀在外。不是么,每逢春秋佳日,便有城内男女游人,结队前来寻幽访胜休闲,已再次成为蜀中名胜之地了。 |